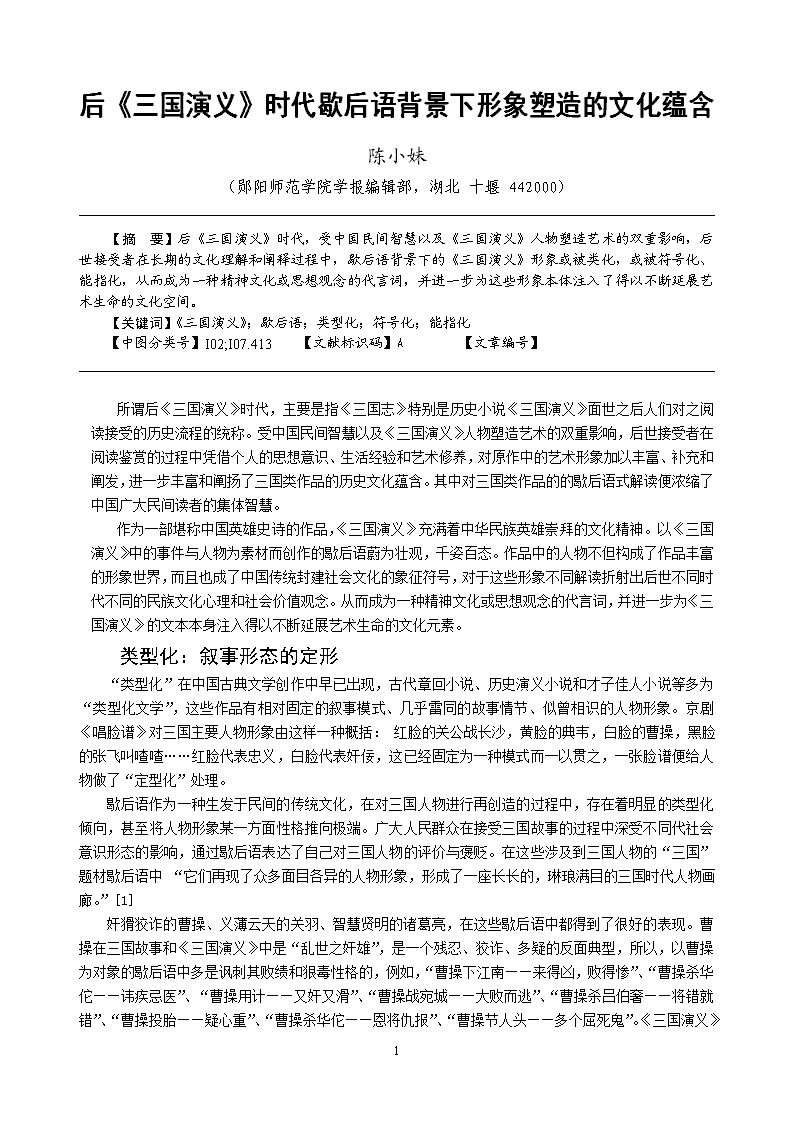- 47.50 KB
- 2022-06-16 13:13:09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后《三国演义》时代歇后语背景下形象塑造的文化蕴含陈小妹(郧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湖北十堰442000)【摘要】后《三国演义》时代,受中国民间智慧以及《三国演义》人物塑造艺术的双重影响,后世接受者在长期的文化理解和阐释过程中,歇后语背景下的《三国演义》形象或被类化,或被符号化、能指化,从而成为一种精神文化或思想观念的代言词,并进一步为这些形象本体注入了得以不断延展艺术生命的文化空间。【关键词】《三国演义》;歇后语;类型化;符号化;能指化【中图分类号】I02;I07.4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所谓后《三国演义》时代,主要是指《三国志》特别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面世之后人们对之阅读接受的历史流程的统称。受中国民间智慧以及《三国演义》人物塑造艺术的双重影响,后世接受者在阅读鉴赏的过程中凭借个人的思想意识、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对原作中的艺术形象加以丰富、补充和阐发,进一步丰富和阐扬了三国类作品的历史文化蕴含。其中对三国类作品的的歇后语式解读便浓缩了中国广大民间读者的集体智慧。作为一部堪称中国英雄史诗的作品,《三国演义》充满着中华民族英雄崇拜的文化精神。以《三国演义》中的事件与人物为素材而创作的歇后语蔚为壮观,千姿百态。作品中的人物不但构成了作品丰富的形象世界,而且也成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对于这些形象不同解读折射出后世不同时代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价值观念。从而成为一种精神文化或思想观念的代言词,并进一步为《三国演义》的文本本身注入得以不断延展艺术生命的文化元素。类型化:叙事形态的定形“类型化”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早已出现,古代章回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等多为“类型化文学”,这些作品有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几乎雷同的故事情节、似曾相识的人物形象。京剧《唱脸谱》对三国主要人物形象由这样一种概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红脸代表忠义,白脸代表奸佞,这已经固定为一种模式而一以贯之,一张脸谱便给人物做了“定型化”处理。歇后语作为一种生发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在对三国人物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类型化倾向,甚至将人物形象某一方面性格推向极端。广大人民群众在接受三国故事的过程中深受不同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歇后语表达了自己对三国人物的评价与褒贬。在这些涉及到三国人物的“三国”题材歇后语中“它们再现了众多面目各异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一座长长的,琳琅满目的三国时代人物画廊。”[1]奸猾狡诈的曹操、义薄云天的关羽、智慧贤明的诸葛亮,在这些歇后语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曹操在三国故事和《三国演义》中是“乱世之奸雄”,是一个残忍、狡诈、多疑的反面典型,所以,以曹操为对象的歇后语中多是讽刺其败绩和狠毒性格的,例如,“曹操下江南——来得凶,败得惨”、“曹操杀华佗——讳疾忌医”、“曹操用计——又奸又滑”、“曹操战宛城——大败而逃”、“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曹操投胎——疑心重”、“曹操杀华佗——恩将仇报”、“曹操节人头——多个屈死鬼”4
。《三国演义》虽有浓厚的尊刘贬曹的倾向,但也客观地表现了他的熟谙韬略,善于用兵的军事家形象。而到了歇后语中,他却与“奸猾”、“大败”、“逃”等词语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十足的奸佞小人与常败将军的形象。小说《三国演义》突出表现了诸葛亮的惊人智慧和绝世才华,在后世的歇后语中,诸葛亮往往是作为“智绝”和“贤相”形象出现的,“诸葛亮做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舌战群儒——全凭一张嘴”、“诸葛亮用兵——神出鬼没”、“孔明给周瑜看病——自有妙方”、“诸葛亮的鹅毛扇——神妙莫测”、“诸葛亮草船借箭——有借无还”、“诸葛亮娶丑妻——为事业着想”、“诸葛亮的锦囊——神机妙算”、“诸葛亮三气周瑜——略施小技”、“诸葛亮焚香操琴——故弄玄虚”、“诸葛亮借东风——巧用天时”、“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生不如死”、“诸葛亮弹琴——计上心来”,在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这些歇后语把人民心目中的偶像诸葛亮推向“智绝”和“贤绝”的神坛。刘备是小说《三国演义》中极力刻画的“仁君”形象,“宽”、“任”、“忠”是其性格的主要特点,在他的身上更多的是体现儒家“仁政王道”的理想,民心的向背是其施政的首要考虑因素。但在歇后语的叙事中,刘备的仁厚在群众看来是软弱,是虚情假意耍赖皮的表现。歇后语“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刘皇叔哭荆州——拿眼泪吓人”、“刘备摔筷子——会遮掩”、“刘备摔阿斗——假买人心”、“刘备的心——无能之辈”、“刘备打马出城西——逃之夭夭”、“刘备轻看庞统——以貌取人”恰恰说明了《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的特点。可见,一味仁厚而缺少性格变化的刘备在群众的接受过程缺乏足够的感动人心的力量。符号化:意识形态的溯形德国符号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把人定义为“使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认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2](P169)现实社会中的人,除了拥有一切动物种属皆有的感受系统和效应系统外,还有自己独有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的主要内容就是语言。在符号学的视野下,写作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孤立的书面文字表达行为,它和其他的符号化活动有共同的运行机制和规则。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作为《三国演义》文本中描刻的艺术对象,他也不能逃脱符号的园囿。在仔细考察这些歇后语之后我们发现,后人在创造这些歇后语时,都赋予这些这些人物以特定历史符号,重建这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封建社会秩序。尽管《三国演义》中刻画的英雄人物形象大多真实地存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但这些形象已经不再和“三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代的人物相符合,确切地说,这些形象在以后每个时代的存在,并不是他们本人的现实存在,而是存在于一种由社会接受而建立起来的文化世界里。刘备、诸葛亮、关羽、曹操等形象存在的形态已和某种文化制度、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人们借以思考、讲述、阐释的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个文化单位。在这些形象的演变过程中,人们赋予这些人物以许多文化符码,即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有的是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有的是后代人赋予的,它们给这些形象本体注入了得以延展的文化生命。从幻化的图景、现实的物象到文本的生成、艺术形象的确立,正是作家操纵着文学创造活动中主体之于客体的审美中介,把人本的能动和文本的受动连接沟通,融为一体,文学作品便是在这种结构的对象化、语符化过程中诞生了。在《三国演义》文本形成之初,所有的艺术形象只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存在于书面上。作品一经面世,处于文学接受阶段,他们便走进了人们的言谈交际,或被进行合目的、合规律的重构,被人们解读传唱;或被纳入现实情境借用来认识事物。从语言符号转变为言语的符号,这些艺术形象已经走上了符号化的历程。诸葛亮这一形象历来被人们视为智慧的化身,所以与之相关的歇后语中也多是表现他的智慧的一面的。“诸葛亮草船借箭——巧用天时”、“诸葛亮借东风——将计就计”、“孔明气周瑜——自有妙方”、诸葛亮征孟获——收收放放“、”孔明弹琴退仲达——好沉着”、“4
诸葛亮皱眉头——计上心来”,从这一组歇后语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诸葛亮已成了智慧的代名词了。关羽则历来是“义”和“勇”的化身,俗语“过五关,斩六将”便是后人根据他的经历创作的,用以比喻创造英雄业绩,建立卓越功勋。“关公面前耍大刀——自不量力”、“关公赴会——单刀直入”、“关云长刮骨疗毒——神态自若”、“关公耍大刀——拿手好戏”、“关羽放曹操——知恩图报”、“关公守嫂嫂——情义为重”、“关云长不杀张文远——念起旧情”,从这一组歇后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人已经赋予关羽以“义”、“勇”的符号,历史人物已经转化为一种审美文化符码。任何人文事物的发展、演变都有一个从具象直观到超象写意的过程。歇后语对人物形象“类型化”、“程式化”的归纳,本身就是一个从具象到超像的抽象化的结果,具有一定的隐喻性和象征性,亦即一种符号化过程。在符号化人物这一“能指”中,“所指”中却包含、隐喻着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物。如历史上有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旷古的诗才和举贤唯能的曹操,历经千载的“再创造”,就演变成了一个“奸相”的代名词,成了一个符号,这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称那些奸猾、多疑且又心怀叵测的人物为“白脸奸臣”或“曹操式的人物”的原因。当然,我们在传播与曹操有关的歇后语时,可以脱离曹操这个人物本身,但不能抹掉人物“躯壳”下的文化联系,因为它的歇后语中人物艺术形象符号化的载体。能指化:审美鉴赏的再创造正如接受美学所揭示的,任何接受都离不开创造,“接受过程不是对作品的简单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的反作用。”[3](P67)在梳理三国题材的歇后语时,我们发现有些歇后语以入完全背离了三国作品的原文环境,如“关公战李逵——大刀阔斧”、“孔明会李逵——有敢想的,有敢干的”、“关帝庙求子——踏错了门”、“关公脖子长肉瘤——脸红脖子粗”、“关公打喷嚏——自我吹嘘(须)”、“关云长放屁——不知脸红”、“扮关公不卸妆——谁不知道你个大红脸”、“关帝庙找美髯公——保险你不扑空”、“关云长说三国——光说过五关,不说走麦城”、“关公照镜子——自觉脸红”、“张飞战李逵——黑对黑”、“张飞的胡子——满脸”、“张飞卖豆腐——人硬货不硬”、“张飞穿针——粗中有细”、“张飞贩私盐——谁敢检查”、“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后世的人们用三国人物书写一个个新的故事,这些故事把三国故事中的人物行为与当下生活“捆绑”在一起,人们用三国故事诠释当下生活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重塑三国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接受美学的理论奠基人姚斯指出:在“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的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4](P168)在现代文化领域里,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等艺术形象不仅以其包蕴的丰富的性格内涵,不断地成为文学研究的课题,而且还作为超越其产生的时间与地域的活生生的人物,成为不同时代人们口头或书面中二度创作的素材,不断地被“再创造”。他们不仅作为自足的文学形象被欣赏与解读,而且也还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神的符号,在文本的不断再生产中反复被增值,为歇后语的衍生提供了现成的母题和人物元素。伽达默尔在其名著《真理与方法》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作品文本的意义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那种在不断变化条件下不同地显现出来的东西,现在的观赏者不仅仅是不同的观赏着,而且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5]读者正是利用“元文本”的意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为歇后语表达思想和情感之需要选取了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现成的人物形象,重新创造了一个个新故事,传达新的思想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霍克斯所说的,“神话之发生作用,在于它借助先前已确立的符号并且一直‘消耗’它,直到它成为空间的能指。”[64
](P123-136)人们先是把罗贯中笔下的刘、关、张等形象当作了“所指”,进而又把他们变成了歇后语中新的“能指”,赋予其新的意义——即新的“所指”。总之,“日常语言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以少量的符号表现无限的内容,特别是隐喻和转喻等诗化的语言,在丰富语言的意义方面展示了无限的潜力”[7](P162)广大人民群众对《三国演义》及三国故事的接受说明“三国文化”有着巨大的魅力,歇后语对三国人物形象的重新依归传统之处,更显示其超出时代、卓尔不群的艺术价值。而人民群众以其民间审美立场,集合民间集体智慧对三国人物形象进行再创造,化雅奥为通俗,扩大了审美领域和审美对象,使三国文化增添了一条传播渠道,为三国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长久地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考文献】[1]、孙红德.歇后语与《三国演义》[J].江淮论坛,1988(1)[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4]、姚斯·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6]、[英]特伦斯·霍克斯.机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王晓升.语言与认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