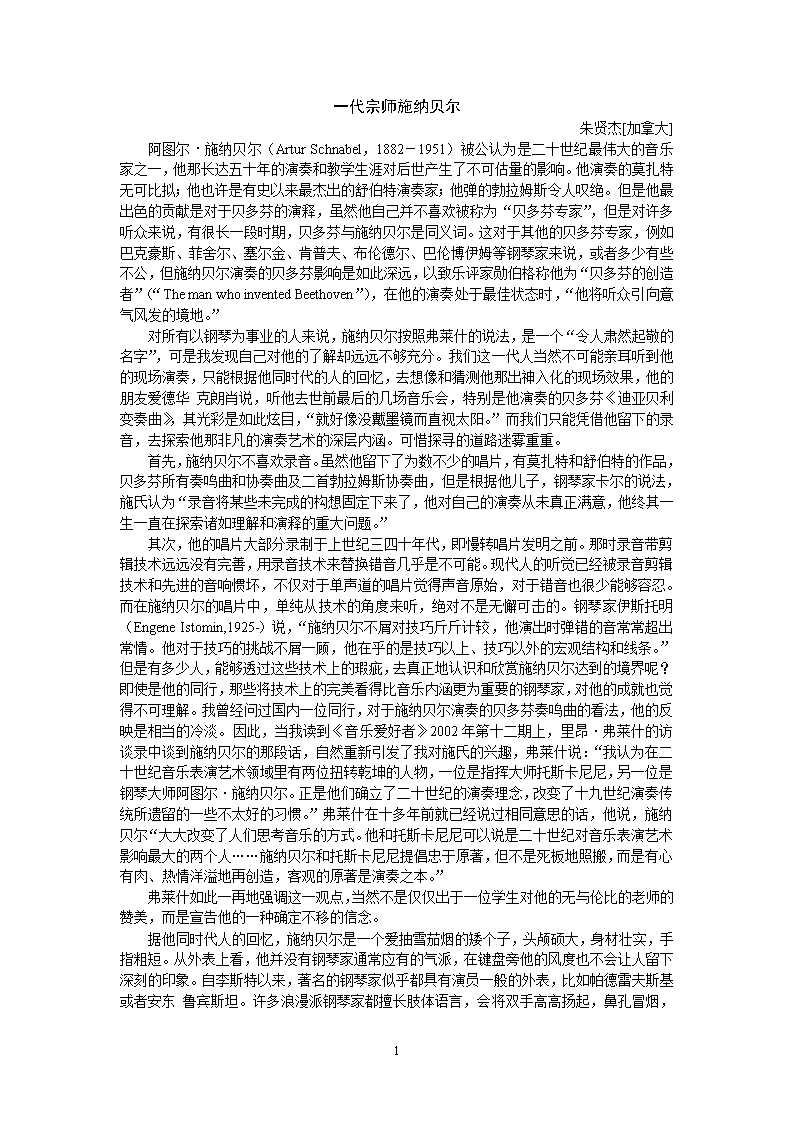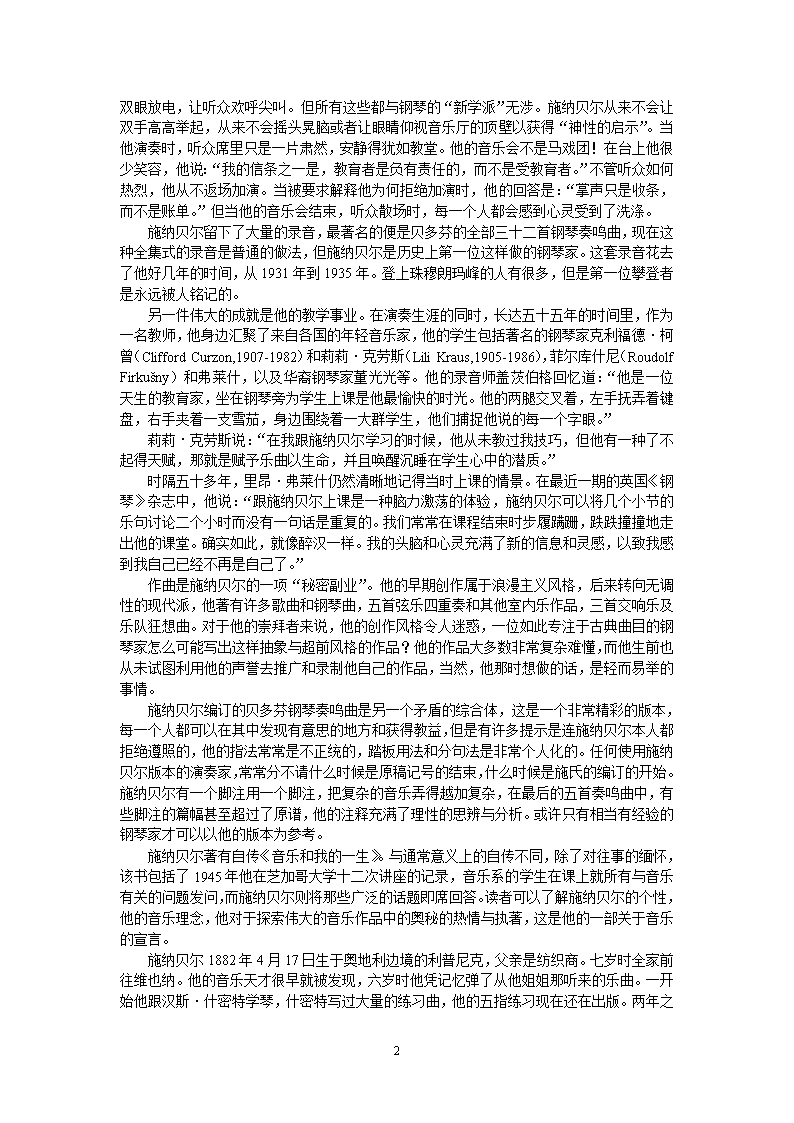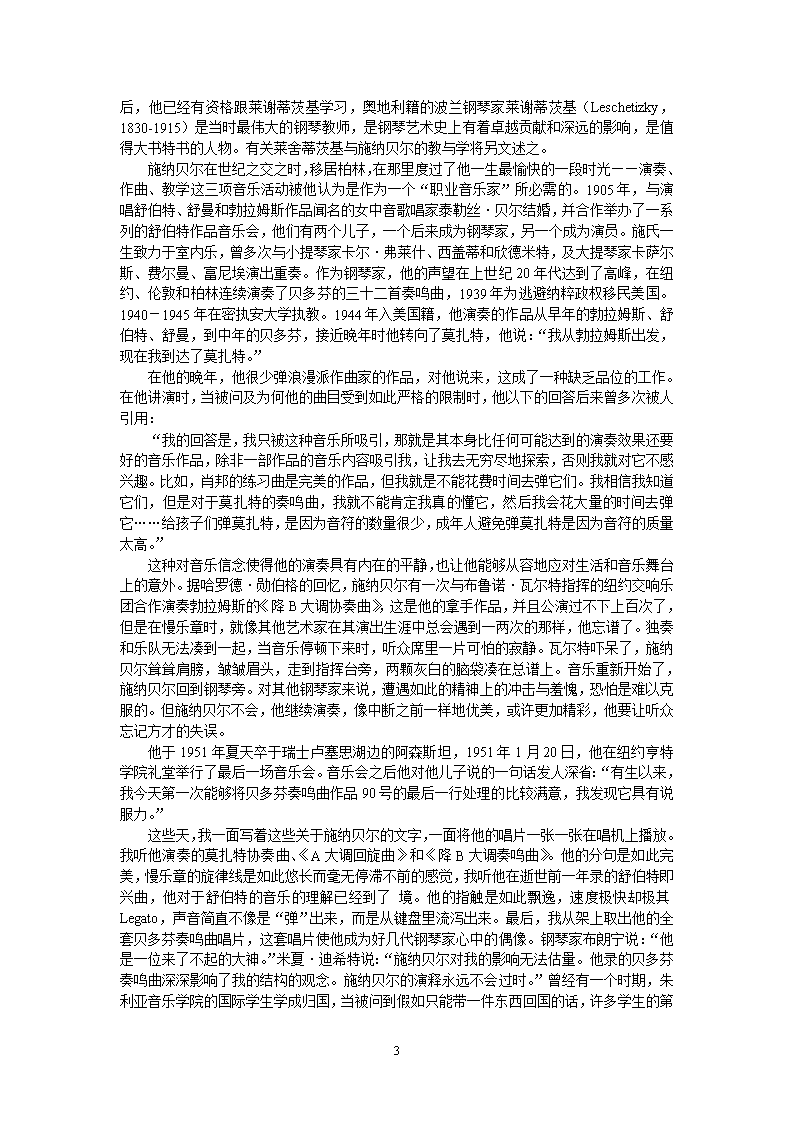- 30.00 KB
- 2022-06-16 12:00:03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一代宗师施纳贝尔朱贤杰[加拿大]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Schnabel,1882-1951)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那长达五十年的演奏和教学生涯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演奏的莫扎特无可比拟;他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舒伯特演奏家;他弹的勃拉姆斯令人叹绝。但是他最出色的贡献是对于贝多芬的演释,虽然他自己并不喜欢被称为“贝多芬专家”,但是对许多听众来说,有很长一段时期,贝多芬与施纳贝尔是同义词。这对于其他的贝多芬专家,例如巴克豪斯、菲舍尔、塞尔金、肯普夫、布伦德尔、巴伦博伊姆等钢琴家来说,或者多少有些不公,但施纳贝尔演奏的贝多芬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乐评家勋伯格称他为“贝多芬的创造者”(“ThemanwhoinventedBeethoven”),在他的演奏处于最佳状态时,“他将听众引向意气风发的境地。”对所有以钢琴为事业的人来说,施纳贝尔按照弗莱什的说法,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可是我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却远远不够充分。我们这一代人当然不可能亲耳听到他的现场演奏,只能根据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去想像和猜测他那出神入化的现场效果,他的朋友爱德华克朗肖说,听他去世前最后的几场音乐会,特别是他演奏的贝多芬《迪亚贝利变奏曲》,其光彩是如此炫目,“就好像没戴墨镜而直视太阳。”而我们只能凭借他留下的录音,去探索他那非凡的演奏艺术的深层内涵。可惜探寻的道路迷雾重重。首先,施纳贝尔不喜欢录音。虽然他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唱片,有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作品,贝多芬所有奏鸣曲和协奏曲及二首勃拉姆斯协奏曲,但是根据他儿子,钢琴家卡尔的说法,施氏认为“录音将某些未完成的构想固定下来了,他对自己的演奏从未真正满意,他终其一生一直在探索诸如理解和演释的重大问题。”其次,他的唱片大部分录制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慢转唱片发明之前。那时录音带剪辑技术远远没有完善,用录音技术来替换错音几乎是不可能。现代人的听觉已经被录音剪辑技术和先进的音响惯坏,不仅对于单声道的唱片觉得声音原始,对于错音也很少能够容忍。而在施纳贝尔的唱片中,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听,绝对不是无懈可击的。钢琴家伊斯托明(EngeneIstomin,1925-)说,“施纳贝尔不屑对技巧斤斤计较,他演出时弹错的音常常超出常情。他对于技巧的挑战不屑一顾,他在乎的是技巧以上、技巧以外的宏观结构和线条。”但是有多少人,能够透过这些技术上的瑕疵,去真正地认识和欣赏施纳贝尔达到的境界呢?即使是他的同行,那些将技术上的完美看得比音乐内涵更为重要的钢琴家,对他的成就也觉得不可理解。我曾经问过国内一位同行,对于施纳贝尔演奏的贝多芬奏鸣曲的看法,他的反映是相当的冷淡。因此,当我读到《音乐爱好者》2002年第十二期上,里昂·弗莱什的访谈录中谈到施纳贝尔的那段话,自然重新引发了我对施氏的兴趣,弗莱什说:“我认为在二十世纪音乐表演艺术领域里有两位扭转乾坤的人物,一位是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另一位是钢琴大师阿图尔·施纳贝尔。正是他们确立了二十世纪的演奏理念,改变了十九世纪演奏传统所遗留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弗莱什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说过相同意思的话,他说,施纳贝尔“大大改变了人们思考音乐的方式。他和托斯卡尼尼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对音乐表演艺术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施纳贝尔和托斯卡尼尼提倡忠于原著,但不是死板地照搬,而是有心有肉、热情洋溢地再创造,客观的原著是演奏之本。”弗莱什如此一再地强调这一观点,当然不是仅仅出于一位学生对他的无与伦比的老师的赞美,而是宣告他的一种确定不移的信念。据他同时代人的回忆,施纳贝尔是一个爱抽雪茄烟的矮个子,头颅硕大,身材壮实,手指粗短。从外表上看,他并没有钢琴家通常应有的气派,在键盘旁他的风度也不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李斯特以来,著名的钢琴家似乎都具有演员一般的外表,比如帕德雷夫斯基或者安东4
鲁宾斯坦。许多浪漫派钢琴家都擅长肢体语言,会将双手高高扬起,鼻孔冒烟,双眼放电,让听众欢呼尖叫。但所有这些都与钢琴的“新学派”无涉。施纳贝尔从来不会让双手高高举起,从来不会摇头晃脑或者让眼睛仰视音乐厅的顶壁以获得“神性的启示”。当他演奏时,听众席里只是一片肃然,安静得犹如教堂。他的音乐会不是马戏团!在台上他很少笑容,他说:“我的信条之一是,教育者是负有责任的,而不是受教育者。”不管听众如何热烈,他从不返场加演。当被要求解释他为何拒绝加演时,他的回答是:“掌声只是收条,而不是账单。”但当他的音乐会结束,听众散场时,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心灵受到了洗涤。施纳贝尔留下了大量的录音,最著名的便是贝多芬的全部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现在这种全集式的录音是普通的做法,但施纳贝尔是历史上第一位这样做的钢琴家。这套录音花去了他好几年的时间,从1931年到1935年。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有很多,但是第一位攀登者是永远被人铭记的。另一件伟大的成就是他的教学事业。在演奏生涯的同时,长达五十五年的时间里,作为一名教师,他身边汇聚了来自各国的年轻音乐家,他的学生包括著名的钢琴家克利福德·柯曾(CliffordCurzon,1907-1982)和莉莉·克劳斯(LiliKraus,1905-1986),菲尔库什尼(RoudolfFirkušny)和弗莱什,以及华裔钢琴家董光光等。他的录音师盖茨伯格回忆道:“他是一位天生的教育家,坐在钢琴旁为学生上课是他最愉快的时光。他的两腿交叉着,左手抚弄着键盘,右手夹着一支雪茄,身边围绕着一大群学生,他们捕捉他说的每一个字眼。”莉莉·克劳斯说:“在我跟施纳贝尔学习的时候,他从未教过我技巧,但他有一种了不起得天赋,那就是赋予乐曲以生命,并且唤醒沉睡在学生心中的潜质。”时隔五十多年,里昂·弗莱什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上课的情景。在最近一期的英国《钢琴》杂志中,他说:“跟施纳贝尔上课是一种脑力激荡的体验,施纳贝尔可以将几个小节的乐句讨论二个小时而没有一句话是重复的。我们常常在课程结束时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走出他的课堂。确实如此,就像醉汉一样。我的头脑和心灵充满了新的信息和灵感,以致我感到我自己已经不再是自己了。”作曲是施纳贝尔的一项“秘密副业”。他的早期创作属于浪漫主义风格,后来转向无调性的现代派,他著有许多歌曲和钢琴曲,五首弦乐四重奏和其他室内乐作品,三首交响乐及乐队狂想曲。对于他的崇拜者来说,他的创作风格令人迷惑,一位如此专注于古典曲目的钢琴家怎么可能写出这样抽象与超前风格的作品?他的作品大多数非常复杂难懂,而他生前也从未试图利用他的声誉去推广和录制他自己的作品,当然,他那时想做的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施纳贝尔编订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是另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版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发现有意思的地方和获得教益,但是有许多提示是连施纳贝尔本人都拒绝遵照的,他的指法常常是不正统的,踏板用法和分句法是非常个人化的。任何使用施纳贝尔版本的演奏家,常常分不请什么时候是原稿记号的结束,什么时候是施氏的编订的开始。施纳贝尔有一个脚注用一个脚注,把复杂的音乐弄得越加复杂,在最后的五首奏鸣曲中,有些脚注的篇幅甚至超过了原谱,他的注释充满了理性的思辨与分析。或许只有相当有经验的钢琴家才可以以他的版本为参考。施纳贝尔著有自传《音乐和我的一生》。与通常意义上的自传不同,除了对往事的缅怀,该书包括了1945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十二次讲座的记录,音乐系的学生在课上就所有与音乐有关的问题发问,而施纳贝尔则将那些广泛的话题即席回答。读者可以了解施纳贝尔的个性,他的音乐理念,他对于探索伟大的音乐作品中的奥秘的热情与执著,这是他的一部关于音乐的宣言。施纳贝尔1882年4月17日生于奥地利边境的利普尼克,父亲是纺织商。七岁时全家前往维也纳。他的音乐天才很早就被发现,六岁时他凭记忆弹了从他姐姐那听来的乐曲。一开始他跟汉斯·4
什密特学琴,什密特写过大量的练习曲,他的五指练习现在还在出版。两年之后,他已经有资格跟莱谢蒂茨基学习,奥地利籍的波兰钢琴家莱谢蒂茨基(Leschetizky,1830-1915)是当时最伟大的钢琴教师,是钢琴艺术史上有着卓越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有关莱舍蒂茨基与施纳贝尔的教与学将另文述之。施纳贝尔在世纪之交之时,移居柏林,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演奏、作曲、教学这三项音乐活动被他认为是作为一个“职业音乐家”所必需的。1905年,与演唱舒伯特、舒曼和勃拉姆斯作品闻名的女中音歌唱家泰勒丝·贝尔结婚,并合作举办了一系列的舒伯特作品音乐会,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后来成为钢琴家,另一个成为演员。施氏一生致力于室内乐,曾多次与小提琴家卡尔·弗莱什、西盖蒂和欣德米特,及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费尔曼、富尼埃演出重奏。作为钢琴家,他的声望在上世纪20年代达到了高峰,在纽约、伦敦和柏林连续演奏了贝多芬的三十二首奏鸣曲,1939年为逃避纳粹政权移民美国。1940-1945年在密执安大学执教。1944年入美国籍,他演奏的作品从早年的勃拉姆斯、舒伯特、舒曼,到中年的贝多芬,接近晚年时他转向了莫扎特,他说:“我从勃拉姆斯出发,现在我到达了莫扎特。”在他的晚年,他很少弹浪漫派作曲家的作品,对他说来,这成了一种缺乏品位的工作。在他讲演时,当被问及为何他的曲目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时,他以下的回答后来曾多次被人引用:“我的回答是,我只被这种音乐所吸引,那就是其本身比任何可能达到的演奏效果还要好的音乐作品,除非一部作品的音乐内容吸引我,让我去无穷尽地探索,否则我就对它不感兴趣。比如,肖邦的练习曲是完美的作品,但我就是不能花费时间去弹它们。我相信我知道它们,但是对于莫扎特的奏鸣曲,我就不能肯定我真的懂它,然后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弹它……给孩子们弹莫扎特,是因为音符的数量很少,成年人避免弹莫扎特是因为音符的质量太高。”这种对音乐信念使得他的演奏具有内在的平静,也让他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和音乐舞台上的意外。据哈罗德·勋伯格的回忆,施纳贝尔有一次与布鲁诺·瓦尔特指挥的纽约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协奏曲》,这是他的拿手作品,并且公演过不下上百次了,但是在慢乐章时,就像其他艺术家在其演出生涯中总会遇到一两次的那样,他忘谱了。独奏和乐队无法凑到一起,当音乐停顿下来时,听众席里一片可怕的寂静。瓦尔特吓呆了,施纳贝尔耸耸肩膀,皱皱眉头,走到指挥台旁,两颗灰白的脑袋凑在总谱上。音乐重新开始了,施纳贝尔回到钢琴旁。对其他钢琴家来说,遭遇如此的精神上的冲击与羞愧,恐怕是难以克服的。但施纳贝尔不会,他继续演奏,像中断之前一样地优美,或许更加精彩,他要让听众忘记方才的失误。他于1951年夏天卒于瑞士卢塞思湖边的阿森斯坦,1951年1月20日,他在纽约亨特学院礼堂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之后他对他儿子说的一句话发人深省:“有生以来,我今天第一次能够将贝多芬奏鸣曲作品90号的最后一行处理的比较满意,我发现它具有说服力。”这些天,我一面写着这些关于施纳贝尔的文字,一面将他的唱片一张一张在唱机上播放。我听他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A大调回旋曲》和《降B大调奏鸣曲》。他的分句是如此完美,慢乐章的旋律线是如此悠长而毫无停滞不前的感觉,我听他在逝世前一年录的舒伯特即兴曲,他对于舒伯特的音乐的理解已经到了境。他的指触是如此飘逸,速度极快却极其Legato,声音简直不像是“弹”出来,而是从键盘里流泻出来。最后,我从架上取出他的全套贝多芬奏鸣曲唱片,这套唱片使他成为好几代钢琴家心中的偶像。钢琴家布朗宁说:“他是一位来了不起的大神。”米夏·迪希特说:“施纳贝尔对我的影响无法估量。他录的贝多芬奏鸣曲深深影响了我的结构的观念。施纳贝尔的演释永远不会过时。”4
曾经有一个时期,朱利亚音乐学院的国际学生学成归国,当被问到假如只能带一件东西回国的话,许多学生的第一选择就是这套唱片。这部录音史上第一套贝多芬奏鸣曲全集的唱片,得以使施纳贝尔做了他的前辈彪罗等人没能做到的事情:通过声音的记录,向所有职业钢琴家和乐迷宣告他对贝多芬音乐的理念,他在演奏的激情、自由与忠于原作之间达到了精妙的平衡。我从他的最后五首贝多芬奏鸣曲听起,我想起了哈罗德·勋伯格的一段评论,这段话可以成为了解施纳贝尔奥秘的一把钥匙,“如果谁学究式地仅仅以有否错音来评判一位钢琴家的话,那么他完全没有领会到施纳贝尔演奏的精华。对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的关注使他将技巧的问题置之度外。他的贝多芬具有无与伦比的风格,智慧的力量和高贵纯粹的分句。重要的是,如果他的手指辜负了他,他的心智从来不会……如果一位音乐家具有真正的鉴赏力的话,就能听到,那是施纳贝尔,在作品110号的慢板中的吟唱,在作品111号最后一页中的清冷的银河星空和作品109号中的抒情纹理。没有诀窍,从不过分,有的只是头脑、心、手指和超人智力的结晶。”发2003年4月号4
您可能关注的文档
- 中国及诺贝尔
- 呼伦贝尔农垦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专用设备项目二次
-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观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 诺贝尔物理学奖之1903年获得者居里夫人
- 呼伦贝尔草原工作站专用仪器仪表项目
- 诺贝尔(第三课时)
- 学习动机在信息技术课堂——奥苏贝尔理念在教学中的应用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作品
-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及其理论
- 第3届林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会总结
- 有退有进 实现呼伦贝尔美丽及发展双赢
- 1997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 2015诺贝尔化学奖
-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人员考试题---呼伦贝尔公共基础考试试题
- 呼伦贝尔市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呼伦贝尔自驾环线